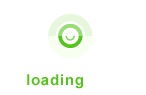《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中的第一篇,这篇列传写法独特,以议论为主体,叙事寥寥数语。其中,司马迁对孔子两句话的疑问,使我产生共鸣。
伯夷、叔齐是殷商时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做父亲的很宠爱叔齐,想要立叔齐为国君。父亲死后,叔齐觉得君位应该是老大伯夷的,要让给伯夷。伯夷觉得父命不可违,于是逃走。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也逃走了。后来两人去投奔西伯昌,到了那里,西伯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正准备进兵去讨伐殷纣。伯夷、叔齐勒住武王的马缰劝谏说:“父亲死了不葬,就发动战争,能说是孝顺吗?作为臣子去杀害君主,能说是仁义吗?”。结果差点让武王身边的武士结果了性命。等到武王灭商建周,伯夷、叔齐认为很耻辱,于是“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靠野菜充饥。饿得不行时,作歌唱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后来饿死了。
司马迁写道: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司马迁引孔子的两句话都出自《论语》。前一句的意思是:伯夷和叔齐不把以往的仇恨(对殷纣暴虐的激愤)放在心上,因而怨恨就少。后一句是回答子贡的话:“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求仁得仁”这一成语,就是由此而来。
司马迁说,他对伯夷的志行深感悲壮,看了他的轶诗又深感诧异。诧异什么呢?因为孔子说,伯夷、叔齐为了自己的理想虽死无怨;可是从伯夷、叔齐的轶诗来看,分明是有怨气的:“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 神农、虞、夏的太平盛世转眼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啊?唉呀,只有死啊,命是这样的苦啊!——这到底是有怨还是没怨呢?
司马迁很给孔子面子,用了个疑问句式,表示不能肯定,可是伯夷的轶诗已说明了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曾困惑着子贡:(为了反对“以暴易暴”竟至于饿死)难道他们就没有怨恨吗?可是很遗憾,孔子为了达到让大家学习伯夷、叔齐好榜样的目的,对伯夷和叔齐的形象进行了“美化”。我们知道,“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孔子所追求的一种思想道德境界。伯夷、叔齐互让君位、不念旧恶维护殷纣的“正统”地位等等行为,在孔子看来就是“仁”,所以他把他们称为“贤人”。如果说他们心有不甘有怨气,那岂不有损他们的光辉形象?因此我斗胆揣测,孔子“求仁得仁,又何怨”这句话,有点言不由衷,有为“英雄人物”遮羞的意思。可“英雄人物”也是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才真实。子贡对老师这句话什么反应,我们无从知道了,但是我们从司马迁笔下看到了疑问——“怨邪非邪?”
对圣人的话进行非议自然不大恭敬,可是从“求仁得仁”这句成语用法的演变上,又不能不说,孔子的言不由衷,的确造成了一种不良影响。求仁得仁,本义是求仁德便得到仁德,比喻理想得以实现。后来用于适如其愿之意。而在用于适如其愿之意时,不少便含有了贬义,有一种“达到了目标,但心中有苦说不出”的意味。这后一种用法,不就是伯夷、叔齐当时尴尬处境的写照吗?更有甚者,有人把 “求仁得仁”和佛家的“报应”、道家的“天道好还”与老百姓说的“活该”相提并论,归于同义,这恐怕更是孔老夫子始料不及的吧?!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肯定伯夷、叔齐的“怨”,与之后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写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在情感上是一脉相承的。他是要写遭到迫害的志士仁人们,对不公正待遇产生怨恨是合乎人情常理的。因为这种“怨”也在司马迁的心中郁积着。
(杨新华)
2006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