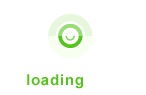汉字的偏旁部首,除了表示意义,有些还能使人联想到相应的形象。因而同偏旁的字的集中使用,每每使字句排列与内容相映成趣,给人以“见字如面”的感觉。正如鲁迅云:“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汉大赋如《子虚》、《上林》的许多段落,就常以此来铺陈状物。后人则将此特色变本加厉地拉杂成整幅对联或诗章,从而获得句意之外的情致。如旧时大车店对联云:“远近通达道;进退返逍遥。”某女自叙身世的上联云:“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前者皆从“走之”,字行排列,虽平仄不叶,却颇能给人以“大车哼哼,遵大路兮”的感觉。后者皆从宝盖,形象烘托出该女子独处幽闺的寂寞牢愁。此手法用于诗中,则同样可产生奇特趣味。如陈朝沈炯《和祭黄门口字咏》云:
嚣嚣宫阁路,灵灵谷口闾。谁知名器品,语哩各崎岖。
诗意在于嘲讽衮衮诸公的昏庸无能:一个个高官显爵,据要路津,以“名器”自诩,谁知说起话来,却满口佶屈,不知所云。诗中四句二十字,若用繁体字书写,竟有四十一个口字,表里相济,形象衬托出尸位素餐者“浑身是口说不清”的尊容,讽刺得辛辣而幽默。
宋代黄庭坚写过一首《戏题》,每句都以同旁字排列:“逍遥近边道,憩息慰惫懑。晴晖时晦明,谑语谐谠论。草莱荒蒙茏,室屋壅尘坌。僮仆侍偪侧,泾渭清浊混。”
内容是写士大夫“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孤愤清贫。首句写行路。字皆从“走之”;次句写情绪,皆从“竖心”;三句写天气,故从日;四句写剧谈,字皆从言;五句写荒草,字皆草头;六句写蜗居,字皆土底;七句写身边僮仆,字皆从“立人”;末句写贤愚混杂如泥沙,故字皆从点水。此诗外形与内容,虽不似《口字咏》之奇谐妙契,但起到了衬托作用。
同偏旁的汉字有限,以之写诗又必须顾及构词的意义,同时又不得不将内容削足适履以迁就形式,因此同旁诗虽不可贵,却属难能,黄庭坚之后,似乎就很少人问津了。
(鄢化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