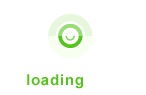我现在住在城里,在城里工作,应该算是个城里人了,可在故乡二十二年的生活经历,给我的思想打上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故乡的山山水水使我魂牵梦绕。因此我觉得我骨子里仍是个农民,就象一首歌唱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一样,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并没有使我忘记自己是从乡野土地上走出来的,我对父老乡亲以及同父老乡亲一样的农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因此对一些城里人对农民的任何歧视和不敬做法,常有如同自己受辱般的感觉。
实际上,城里人早先也都是乡下人,即便自己不是,但他们的父辈或父辈的父辈,说不定就是乡下人,当年一样的蓬头垢面,一样在城里小心翼翼然而仍不断受到白眼和喝斥,才在城里落住了脚。可是,时间一久或已经隔代了,便以“乡下人”为耻了,口口声声“乡下人”长、“乡下人”短的,以贬损“乡下人”,来显摆自己“城里人”的“高贵”身份。如果仅仅是口头上的贬损倒还罢了,可有人还要落实到行动上。
一次我到一单位办事,碰巧有一女士正眉飞色舞地在向她的同事描述家里最近来了丈夫乡下亲戚的事儿:“你不知道,一进门地上就有拖鞋,他也不知道换,一走一个鞋印,一走一个鞋印,看着简直烦心死了,啥也不懂。后来我干脆拿着墩布,他在前边走,我就跟在他后边拖……哈哈哈……”看着那张还算周正、正为自己的行为开心不已的笑脸,我竟有上去给她一巴掌的冲动!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理,使她为了留在地板上的一两个鞋印,竟可以无视别人的尊严?我相信,如果到她家的是她的顶头上司,那必将是另一番情景。
我的一个“发小”朋友,现在两口子在城里靠疏通下水道谋生。他经常对我说,你们城里人毛病就是多。他最近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一天他接到一个传呼,便跟着老婆一块赶了过去。那是一个三层的楼房,打他传呼的是三楼的女主人。告诉他说,因下水道堵了,一楼便关了通向楼上厨房的水阀,已经好几天了,找人家,人家说又不是我一家用。为了用水,只好自己打电话找人疏通了。我这位朋友疏通一番以后,让试一试,一楼还是说不行,再疏通再试,还说不行。我朋友就要进去看看,可一楼女主人不让他进门,说你的鞋上都是屎呀尿的。可实际上,她也一直家里家外地来回走来着。一直耗磨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没辙了,他强闯进去用皮揣子一揣便透了,原本就是她家厨房下水的竖管儿堵了。“最后我洗手都是跑到三楼洗的”,说到这儿,我的朋友眼睛潮湿了,他说,“在城里挣钱多少不说,有人不拿你当人看最叫人受不了”。
这种不把“乡下人”当人看的现象,在城市并非绝无仅有。今年“两会”前夕,青岛的一位市民就曾在报上提议,在公交车上设立民工专区。他说,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的市民素质步步提高,着装越来越干净。而在青岛打工的民工却“素质低,不讲卫生”,在公交车上隔出小块区域专门供民工使用,“可以减少市民对民工的厌恶感,消除双方的隔阂和矛盾”。此言一出,反响强烈。我想在那些赞同者的眼里,民工就象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黑奴”,而自己则是“白人”,在他们的脑子里,我比你高一等。
民工素质低不低我不敢肯定,可我敢肯定的是,提这提议的人却是明显的“素质低”;公交车设立民工区,是不是会减少市民对民工的厌恶感我不敢说,可我敢说的是,这样做一定会引起民工对市民的厌恶感,不是“消除双方的隔阂和矛盾”,而将恰恰相反。
农民素质低,并不是他们的过错,况且从做人和道德的角度说,他们的素质一点也不比某些城里人低。那些叉着腰空喊让民工讲卫生、提高民工素质的人,你去摸摸吧,他的肚子里一定还有没消化掉的鱼肉。“乡下人”和“城里人”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不尊重甚至歧视“乡下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歧视自己的父辈和祖辈,而看不起自己的父辈或祖辈,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合适的。
(杨新华)
2002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