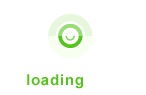古代的读书人,大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学而优则仕”,不知让多少读书人神魂颠倒,为了一个“仕”字,而去追求所谓的“优”。
如何才能“优”呢?那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并不惜焚膏继晷,头悬梁、锥剌股地折腾。宋代王禹的一首《清明》诗,道出了其中的况味:“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到最后,有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了;而有人却皓首穷经,仍为布衣,只能感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宋代还有个叫晁冲之的,一生读书也没有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晚年他在一次黎明时分的旅途中,看见一家人家亮着的灯光,联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禁感慨良多:“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读书一旦被当作“敲门砖”,这书就读得憋闷而苦涩,难怪有人拿起书本就瞌睡,就无意绪,一年四季都打不起精神:“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初长正好眠,秋又凄凉冬又冷,收书又待过新年”。
可是读书人一脉相承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忠君爱国意识和忧患意识,却是渗透在骨子里的,而他们拿封建时代黑暗的社会制度又无可奈何。报国无门的憋屈,官场遭贬的忧愤,使不少旧时读书人发出“不才明主弃”之类的牢骚,和“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之类的故作放达语。到这时,儒家提倡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就开始起作用了——既然不能“兼济天下”了,那也就只好“独善其身”了。失意的读书人这时才把名利暂搁一旁,以读书修身养性;而功成名就的读书人,这时也能放松心情,在书中“精鹜八极,心游万仞”了。
他们有的把书比作朋友,不时与之促膝交谈:“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于谦《观书》),或说“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陈继儒);他们有的与书朝夕相伴,在书的世界里流连忘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陆游);也有的厌倦了尘世的喧嚣,在书里寻找内心的宁静:“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李乐);读书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相邀文友一起“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有人甚至把读书推崇到了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地步,明人胡应麟说:“余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韶》《頀》,览之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黄庭坚则对读书能培养人的精神气质非常看重,他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陈继儒说:“神仙不读书,亦是一俗汉,所谓顽仙不如才鬼耳。”而苏轼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将其概括为“腹有诗书气自华”。不少人已经把读书披阅,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了。北魏的李谧杜门却扫,弃产营书,他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很是欣赏,每每自叹:“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
由于有人爱书如命,因此一些人也便有了诸如“书痴”、“书淫”、“书厨”、“书库”等等的雅号。
在读书方式上,有人不怎么讲究,比如欧阳修谓读书有“三上”:“枕上、马上、厕上”。可也有人就没这么随便,他们视读书为雅事,不能不讲读书的环境,不能不讲情调。所谓“读易松间、谈经竹下”,“读书于雨雪之夜”,“雪夜闭门读禁书”,都是这样的意思。甚至连什么时节,宜读什么书都有说法:“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有人读书前还要焚香沐手,这固然有惜书的意思,可实际上也是在营造读书的气氛。不是有一句“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话么,这一度是古人向往的阅读氛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读书人那种自视甚高的心态。可真要有“红袖添香”的时候,我怀疑那多半是提醒你该睡觉了,聪明的“红袖”们会让你觉得,她是在添香而不是添乱,是在磨墨而不是磨牙。可那一颦一笑左右你的视线,这书还如何读得下去?
摆脱了名缰利锁的羁绊,读书人在“竹露松风蕉雨”和“茶酒琴韵书声”中逍遥,读书也不必那么一味地热屁股贴冷板凳了。“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蔡确),何等的自适随意。读书每有所得,更是最大的快乐。陶渊明是“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徐惟起则形容“虽丝竹满前,绮罗盈目,不足喻其快也”。心情舒畅后,这种读书之乐,一年四季都可以享受:“读书之乐乐何如, 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 拨琴一弄来熏风;读书之乐乐陶陶, 起弄明月霜天高。读书之乐何处寻? 数点梅花天地心”(朱熹《四时读书乐》)。
当然,古代读书人除书之外,大都还有另一种爱好,就是放怀自然,寄情山水。就象晦庵和尚说的:“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
(杨新华)
2002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