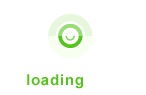二爷姓秦,大名秦二友,其实他也就是根独苗,并没有什么兄弟姊妹,不知为什么老人给他起了个带“二”的名字。
听说二爷是他父亲上山干活时捡来的,当时有几个老鸹正围着襁褓中的他转,他的哭声惊动了他父亲。走近一看,他的脸上血沥呼拉的,已经被老鸹啄过。那时节,他父亲和他母亲结婚三年了,可他母亲肚里仍没个动静。所以,当他父亲发现他是个带“把儿”的娃娃时,当时心就动了,把他抱回了家。所以没人知道他的生身父母是谁,后来有人猜测他是没出门子的大姑娘的私生子。——小时候,听老一辈人讲起二爷脸上疤痕的来历时,总有几分不屑地把上辈人传下的这个故事再复述一遍。
二爷在姓秦的家族中辈份最长,和他岁数差不多的人,有的也该叫他爷,更甭说一些后生小子了。也许是叫着顺口吧,从我记事起,就老听人们称他为“二爷”,无论是他本族还是外族的人,就像“二爷”是他的名字一样。
二爷读过私塾,在农村也算个识文断字的人。不过二爷读的是一些闲书,而且写字也不行,所以庄户人家过年写春联、婚事写喜帖、白事记帐什么的,还是找老庆爷。老庆爷早年做过私塾先生,开过中药铺子,乡亲们有个头痛脑热的找他开个方子,他也从不推辞,所以乡亲们对他很是尊敬。加上老庆爷平易近人,村里的一些岁数差不多的人,常在冬天的晚上到老庆爷家里扯闲篇儿。另一处冬天消长夜的地方是生产队的牲口棚,不过,去那里的人成份就复杂多了,由于是公共场所,虽然闻着热烘烘臭哄哄的牛粪味儿,可气氛显然比老庆爷家要轻松得多,可以吵闹,也可以放肆地大笑。
二爷是这两个地方的常客。他是生产队里唯一的车把式,他晚上到牲口棚去,一来可以顺便看看他心爱的牛——“阴阳角”;二来他一到这里总能找回点尊严,一些毛头小伙子总是缠着要他讲古。但到老庆爷家就不一样了,那里总有一种“沙龙”的氛围,而二爷总是邋邋遢遢,鼻涕象长年挂在前川的瀑布,他从人们的眼神里能够感觉出别人对他的鄙夷,无形中就有一点自惭形秽。
二爷最喜欢讲的“古”是《隋唐演义》,而讲的最得意的要属讲秦琼了。至今我还记得他那几句:“那秦琼,姓秦名琼字叔宝,是‘锏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的好汉——哪位不知道山东秦二爷?!”每当说到这几句,他总是神采飞扬,那份自豪让人明显地感觉到他也是“秦二爷”,俨然自己也就成秦琼了似的。完了他还要把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流出来的鼻涕猛地吸溜进去——霎时,牲口棚便爆发出强烈的哄笑和咳嗽声,以至要乱哄哄地持续很久。
二爷还有一个让人瞧不起的毛病是嘴馋,好喝“蹭”酒,乡亲们把这种行为称作“溜板凳头”。不管谁家里有什么事儿,只要有酒喝,他都会“闻着味儿”走,借故过去,坐下就不走。其实,谁也倒不是怕多一个人喝酒,关键是人家本来要在喝酒当中说的话,因为他在跟前,就没法说了,这一点最是讨人嫌了。
传说晚上他到老庆爷家去,有时去得很早,并且到那儿就坐在左边的那个圈椅里。椅子后边有个小缸,里面盛着芝麻,他可以随手向下一伸胳膊抓一把,再放在衣兜里,过后慢慢当零嘴儿吃。反正屋子里一灯如豆,不会担心有人看见。可日久天长,缸里的芝麻却见少。老庆爷想,这缸这么滑溜老鼠也上不来呀,便想到了二爷这毛病。后来他跟其他乡亲一说,其他人也异口同声地说肯定是他干的。有人想了个主意,让老庆爷把小缸里的芝麻倒腾到别的地方,里面换成一缸水。起初老庆爷觉得这样未免不厚道,可架不住那人的撺掇并亲自动手帮忙,说这样可以看看竟究是不是他,并且对他也是个教训。果然,那天晚上二爷又去了,并且又占到了那个位置,当大家谈兴正浓时,就听得“扑嗵”一声,大家故作惊讶地问:“什么声音?好象是二爷!”并都凑过去,只见二爷右胳膊的半截棉袄都在往下流水。老庆爷还赶紧替他打圆场:没事没事,二爷不经心把手伸到咸菜瓮里了。
有一阵子,老庆爷头上长了疖子,便往白矾上吐唾沫抹疖子,说是可以消毒止痒。不用时,就放在一个倒扣着小茶碗的碗底上。二爷早就盯上了这个小东西,以为是块冰糖。有一晚终于按捺不住,在没人注意时,拿起放在了嘴里。这一放,便品出了味道的不对,后又装着擦嘴,把那东西吐在手心扔在了地下。当晚睡觉时,老庆爷再想擦擦疖子,可碗底上却没了那东西。第二天扫地时,发现那东西在二爷昨晚坐过的椅子底下,便明白了一切,心里也不免暗自好笑。
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人们对二爷的看法才算有了改变。那一年,生产队里二爷心爱的牛“阴阳角”死了,队里在井台边开始对它进行肢解,分肉吃。可是在念到秦二友的名字时,叫几遍却没人答应。大概队长也悟到了什么,再念其他户主的名字时,也没了刚才的兴奋劲了。
后来听说,那天二爷把吵着要去领肉的孙子掴了一巴掌。几天以后,人们再见到二爷时,二爷瘦得几乎脱了相。再后来,人们才听说,那头牛曾救过二爷的命。
(杨新华)
2002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