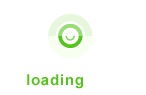过年杂忆
过年杂忆
又该过年了。
可是现在除了马齿徒增的感慨,却没有多少过年的兴奋了,有的却是关于过去过年的回味。 小时候一进腊月,就会听母亲说“喝了腊八粥就该过年了”。实际上,喝腊八粥时并没有一点年味。不过对于小孩子,这仍然是个“里程碑”式的日子——毕竟离年越来越近。老家人说腊八是“枣树的生日”。这一天的早饭总是要熬小米粥,里面还要加上豆子、红枣。粥熬好后,母亲总是先盛出半碗,再特意地多捡上几颗枣,让我和姐姐去给枣树“上供”。我家西园有好几棵枣树,我们会用筷子先往树叉上挑上点米粥,再用手拿起枣往上面抹,让枣树“吃”,听说这样来年枣就会结得稠。高一点的枣树,我们够不着它的“嘴”,就往它身上胡乱抹一通,也是“心到神知”的意思,吃到吃不到就不管那么多了。
腊月十五前后,如果有风和日暖的日子,就该“扫房”了。“扫房”可以说是过年“准备工作”中最累最脏的活,先要把被褥晾晒出去,接着是把杂七杂八的物什倒腾到院子里。一年的烟熏火燎、尘飞鼠盗,梁头珠丝暗结、墙角潮土塔起,实有清理一番之必要。用根竹竿绑上个笤帚疙瘩,上下一通扫荡,等人再从屋子里出来,就只有两只眼球是干净的了。下半晌再把倒腾在屋外的东西擦抹一遍,再倒腾到屋里归置好了。然后看着新糊上的窗户纸,屋里哪跟哪都整整齐齐的,心里便隐隐有了种对过年的期盼。
再往前的腊月二十三,是个重要日子,有的地方甚至称之为“小年”。我们老家的俗语说:“糖果祭灶二十三,媳妇不来把门关。”听上辈人讲,这句话的意思是凡是这一年娶的新媳妇,在腊月二十三这一天都应回到婆家。我琢磨着,这可能是因为腊月二十三是进入春节前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祭祀大典”,而且灶神要到上天汇报全家每个人的思想品德情况,自然应该全体到场以示崇敬,免得他一不高兴背后念秧子。
此后一直到除夕,都是置办年货、准备吃食——碾糕面、蒸馒头、赶集割肉……。街上孩子们唱的歌谣时时会传进耳朵——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远近也偶尔会有一两声的鞭炮响,为年前的忙碌作一下点缀。 年三十一早,街上便抻起了挂灯笼的绳子,看着五颜六色的纸吊挂儿在寒风中飘来飘去,不由得就会心旷神怡。这一天上午,是曾做过教师的父亲一年中颇为得意的时候,因为读过的书到这时总算派上了点用场,乡亲们会拿着大红纸找父亲写春联。屋子里常常站了满屋子的人,写完一条就晾在院子里一条,这个走了那个又来了,一直得写到吃晌饭。下午,家里开始包饺子,母亲会安排我把院子和门外清扫一遍。窗台上、石桌上、旮旮旯旯用笤帚密密扫过去,能清出几筐土去。然后再用清水洒一遍地,看上去的确清爽得很。吃了晚饭,会到街上去看灯,去听远远近近的欢声笑语,去闻弥漫在空气中的炮硝味、蜡油味和燃香味,那就是真真切切的“年味”儿。这一夜,很多人会彻夜不眠守岁,鞭炮声此起彼伏,并在五更时,暴响成一片。“天地会”供神的小屋里,“大头”、“接头”、“送头”三家的青壮年男人,在晚上挂完灯后,会用木柴点起火“值更”。并在半夜至五更这段时间,分别沿街敲三次锣,以提醒时间。人们也会用“刚敲了头遍锣”、“已经敲了二遍锣了”等,来判断时间的早晚。
想过年,盼过年,真到了正月初一,却发现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之间便过去了。儿时盼过年的另一种想法就是过年可以解解嘴馋,因为一年到头也就过年可以名正言顺地吃白面,至少正月初一一天顿顿是白面,白面饺子、白面馒头,还可以吃上肉。另外还有炒好的花生、瓜子,衣裳的口袋里总是鼓鼓的,直吃得咳嗽上 “火”,口角生疮。
正月初一有很多的禁忌。起初是奶奶后来是母亲会嘱咐我们这一天少说话,生怕童言无忌出口成谶,给家里带来一年的坏运气。比如不能说“没有”、“完了”等等,只能说吉利话。有时,本来无心的问话,也会被母亲以“多着呢”、“好着哩”等吉祥语相答,听后果然便有了种神秘和神圣的感觉。记得五更里,听哪家开始点炮,小伙伴们便一起跑过去捡落地没响的小鞭炮,并称之为“绝捻子的”。却常常让人给轰出来,原因就是一兴奋会口不择言:“这一个‘绝’的”,“这又有一个‘绝’的”,触犯了忌讳。再就是正月初一忌打坏东西,不小心打坏了,也要赶紧说“岁(碎)岁(碎)平安”,以图用吉言相抵,庶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那一年正月初一,母亲拜观音菩萨,把盛着肴馔的碗往佛龛上放,由于那佛龛是在院子的南土墙上挖出来的,本就不太深,再加上下雨把底面冲刷得有了坡度,碗没有放牢,掉在下面摔坏了。这件事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一直压在心里。也就这一年母亲得了病,便笃信自己的病治不好了,她不让送她去医院,直至病重去世。病床上,她才把过年时发生的这件事说了出来。
初一拜年,是乡亲之间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如果这一年中两家产生过矛盾,过年的时候让晚辈到对方家里去拜年,就是一种很好化解矛盾的方法。当然,也有趁拜年之机显示家族势力的,五兄六弟七狼八虎,一站一院子,跪倒一大片,很难说不是一种炫耀,不由人啧啧羡叹,也不由得生出几分畏惧之心来。
小时候家乡过年主要的娱乐活动是荡秋千和踢“轳辘悠”。秋千架下常常聚集着男男女女,青年小伙子在大姑娘小媳妇们面前逞能斗强表现英雄之气,把秋千荡得几与横梁相平,以把她们惊得失声尖叫为快意。踢“轳辘悠”则属于“恶作剧”一类的游戏,一边一个立柱,上边横绑一根串过轳辘的铁棍,轳辘上面搭一根井绳,井绳的一头再有一根小木棍串过。规定人身子必须在两根绳子的外侧,人站在木棍上,双腿夹住绳子绷直,然后再倒着手向下拉绳子的这一端牵引着身体上行,以能拿到横梁上的奖品为优胜。但十有九个在刚离开地面时,身子便严重失衡向后仰着摔下来,从而引起瞧热闹人的开心哄笑。晚上,小伙伴们有时会在窗户前玩一种极类皮影的“小人儿打架”或用手变“狗叫”、变“兔子洗脸”的游戏。一个人端着油灯,一个或两个人表演,其他的则在屋子外观看。天寒地冻的也不怕冷,屋里屋外的疯跑,饶有兴味。
老家的规矩,不出正月十五,凡走亲访友都要先给对方的长辈拜年,可见正月十五之前都是在“过年”。此后虽还有什么正月十六“烤门前火”、二十五过“填仓节”,但心劲已在正业上,实在不能算是过年了。
如今,物质、文化生活之丰富已非昔日可比,可越来越觉得现在过年没“年味”了。想想“年味”是什么呢?可能就是那些精心准备的过程,就是那些种种的规矩和禁忌,就是那些群体聚集在一起的热闹吧?
(杨新华)
2005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