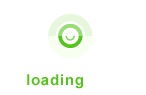三十多年过去了,教过我的老师想想总也有几十个。有不少老师很有特点,他们在课堂上言谈举止的一些细枝末节常常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我的启蒙老师实在算不上最有特点的,但每当想起,她的音容笑貌都如在眼前。我想,这也许因为她是我的第一个老师,而孩提时代对事物的感知能力又特别强的缘故吧。
她叫王兰淑,三十来岁的样子,中等身材,长方脸,皮肤有点黑——虽然在室内工作,可看上去,她的肤色倒像是个地道的农家妇女。她留着向后梳的齐肩直发,两鬓各有一个小发卡把乱发拢住。她不是那种好打扮的人,而且他的装束也尽量与普通的农家妇女接近,可她的干净利落,还是能让人看出她与农家妇女的不同来。
当我由姐姐领着,扛着父亲临时给我拼装起来的新凳子,在学校院子里见到王老师的时候,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才算稍稍平静了些。她脸上的笑,让我觉得亲切,她摸我头顶的动作,就像母亲一样让我有了安全感。
听说我们的学校原先是一个寺院,我们的教室就是原来的“大雄宝殿”,这也是寺里唯一留存的建筑,牌匾早已没有了,因为它座北面南,那时学校里的人都叫它“北大殿”,以区别于别的普通教室。北大殿除了地上有几根柱子显得有点碍事外,倒是很宽敞,所以里面安排了两个班级,另一个是四年级,王老师同时是这两个年级的班主任。大殿的东西面墙上各有一块用水泥抹制的、刷上锅底灰的黑板,两个年级的学生背对背坐着,中间有着两三米宽的空地。王老师在这面讲一节课,然后留一节课的作业,下一节课再到那面去讲。
我特别喜欢听王老师领读的声音,语文课上,她把一些生字写在黑板上,然后开始领读,我们随后跟着念:太——(太)!太阳的太——(太阳的太);月——(月)!月亮的月——(月亮的月)……。那清亮的女性嗓音,悦耳动听,每次朗读,我们这帮孩子总是精神振奋,读得十分带劲儿。有时王老师在领读几遍以后,会把领读的“权利”交给我,这对虚荣心十分强烈的孩子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荣幸,而不少孩子为此除了对我羡慕,还纷纷向我示好。王老师对学生作业的要求首先是整洁,我记得她常会拿着我写的语文作业本,向同学们展示说:我们写字就跟种菜一样,不要密密麻麻粘在一块,要像他写的这样,横着看、竖着看、斜着看都是行,都很整齐。应该说,是王老师的鼓励,让我有了学习的兴趣和自信。
印象中,王老师对我几乎没有批评,总是一幅和蔼可亲的样子。但对一些调皮捣蛋或成绩不好的学生,她也有其严厉的一面。刚入学的时候,我们还穿着开裆裤呢,有的孩子自制能力差,课间贪玩,等上了课内急,又不敢告诉王老师,常有尿裤子的事儿。如果瞒不住,被其他孩子“举报”了,王老师就会“揪”起他,让他岔开腿站到前面的炉子上去,这时总会引起孩子们开心的笑声。更为严重的是,有一次,一个孩子竟然从自己的身体里拽出一条蛔虫,扔到了凳子下面,于是整个北大殿笑声、惊叫声、起哄声乱成了一锅粥。王老师更是显得怒不可遏,她“揪”起那个孩子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一直到门外才听她吼道:“找两根棍子来!快给我夹出去!”王老师揪人的方法比较特别,她是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先捏住对方的耳唇,然后再一转腕子,用中指端住对方的腮帮子,我们称其为“端灯”。有一次,我们背后四年级有个叫二臭的学生,不知什么原因惹王老师生气了,王老师去端他“灯”的时候,他居然叫道:“唉哟,老师你小点劲儿,我耳朵冻了!”惹得两个年级的学生哄堂大笑,连王老师也“卟哧”一下笑出了声,并松开了手。“我耳朵冻了”曾被奉为“经典”,在学校盛传一时。“文革”开始,王老师挨批斗了,有人鼓动二臭去揭发王老师,可是他没有。后来有人还看见他偷偷去给王老师送过家里树上结的苹果。
王老师常帮一些家境特别困难的学生垫付学费和书费,我记得我曾为家里拿不起两元钱的学费,哭着喊着躺在地上不起来。后来,母亲领着我到学校找王老师说情,王老师当时就表示说“不要紧”,并为我垫付了2元钱。为此,母亲便让我和姐姐把家里刚摘的南瓜去给王老师送两个。我们不好意思,晚上只是悄悄地把南瓜搁在了王老师的窗台上,就回来了。
王老师的丈夫是干什么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婆家离我们村有二十来里地呢。王老师的大女儿和二女儿都是寄养在我们村老康家里带着。我记得那时她到老康家去,或从老康家到学校去,如果正赶上吃饭的时候,每经过一个“饭场”,街两旁的乡亲们都会齐齐地端着碗站起来和她打招呼:“王老师,吃了没?在这儿吃点吧?”王老师也总是同他们一一地点头寒暄。走过去以后,乡亲们还常常要评价两句:“王老师这人儿可不赖,挺‘豁啦’(豁朗、没有架子的意思)。”
“文革”开始后不久,王老师就调走了,算来她教了我有两年多时间。有人说她调到县上去了,也有人说她回原籍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从上大学到参加工作,一直存着去找找王老师看望看望她的念头,却终没有成行。她也许早已忘记还有我这么个学生了,可是在我心里是永不会忘记她这个启蒙老师的。
王老师,保重!
(杨新华)
2002年9月8日